摘要 為什么處在國際分工產業鏈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對全球化、賺著微薄加工費的中國卻義無反顧地擁抱全球化?從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的全球化進程,目前正面臨著走回頭路的壓力,而最響亮的反對聲音,...
為什么處在國際分工產業鏈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對全球化、賺著微薄加工費的中國卻義無反顧地擁抱全球化?從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的全球化進程,目前正面臨著走回頭路的壓力,而最響亮的反對聲音,居然來源于過往全球化最積極的倡導者英國和美國,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就是明證。2017年法國、荷蘭、德國等歐洲重要國家的大選,也必將是對全球化進程的新一輪“壓力測試”。
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西方的反全球化聲浪就日益高漲,但主要限于學術、輿論和民間層面,現在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層面,充分說明了全球化在西方社會“不得人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這個全球化的后進者和規則的接受者,正在成為全球化最積極的倡導者和最可能的領導者。
1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認為“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呼吁世界各國“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并強調“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
就在習近平演講的當天,中國國務院發布通知,允許外商可在A股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市,并在“新三板”掛牌,還可發行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和運用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融資。此外,還放寬銀行、證券公司等的外資限制,開放外資進入會計審計、建筑設計、評級服務等領域,這一舉措,在遏抑資本外流之余,也有向世界顯示中國開放誠意的意思。
在政策層面,中國近年來還出臺了“一帶一路”戰略,牽頭和參與建設了金磚銀行、亞投行等國際機構,和韓國、澳大利亞等多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并積極推動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簽署。在國內,自2013年以來中國已經在上海、廣東等地設立了11個自貿區。而單單廣東自貿區(由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和深圳前海三部分組成),去年1—11月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就有4070家,同比增長77.3%,合同外資366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72.8%。
那么,為什么處在國際分工產業鏈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對全球化,而賺著微薄加工費的中國卻在義無反顧地擁抱全球化呢?
對外開放在中國是種“政治正確”
首先,中國和西方面對全球化的心態不同。普遍認為,全球化有利于西方受過良好教育、有國際化工作機會的個人和能進行全球化資產配置的跨國資本,而對一個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美國人來說,全球化讓他們不得不卷入和全世界廉價勞動力的競爭中,這讓他們覺得利益被損害了。“鐵銹帶”的美國人因此選擇支持特朗普;歐洲研究機構勃魯蓋爾(Bruegel)對英國脫歐公投的研究也顯示:在貧富差距大和顯著貧困的地區,脫離歐盟的票數居多。據統計,2005-2014年世界25個高收入經濟體有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停滯甚至下降。顯然,全球化在西方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失意者的相對剝奪感和不滿。
而中國的貧富差距程度雖然并不比西方低,也同樣出現了富裕階層和貧窮階層、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損者、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受教育和沒有受教育、年輕人和老年人、城鎮和鄉村之間的分化和鴻溝,但各個群體大體能相安無事,并沒有出現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嚴重對立局面。這是因為中國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百廢待興,起點很低,但迅速抓住了發達國家制造業轉移和移動互聯網革命等機會,加上民眾的勤勞和紀律性,經濟實力迅速提升。即便到了今天,經濟的增速已經明顯下降,但總體上蛋糕仍在不斷做大的過程中,雖然大多數人對腐敗、收入分配不公嘖有煩言,但也同時承認,與改革開放之初的赤貧狀態相比,自己的生存狀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與此同時,中國的教科書和官方宣傳也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對民眾進行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在不斷加深”、“全球化進程不可阻擋”之類的教化,并著力于展示中國在全球化中的獲益和取得的進步,這些宣教加上那些實實在在的成就,使得推進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在中國差不多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其次,中國和西方的社會氛圍不一樣。二戰后西方興起福利主義,強調政府對人民的種種義務和責任,加上選舉政治的影響,個人為自己負責的精神漸漸減退,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訴求比天大,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社會和別人。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政客操弄民粹、尋找替罪羊、禍水外引的做法就很容易大行其道。
而中國盛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人力爭上游,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被認為是理所當然,這一方面強化了中國勞工和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一個人一旦在競爭中失利,更多會責備自己,從自身找原因,并傾向于通過親戚朋友網絡來獲得幫助,東山再起,很少人會在這方面對政府寄予厚望,一般也不會諉過于來自外部的競爭。事實上,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政府抱敬而遠之的態度,對政府的要求基本限于“你不要來找我的麻煩就好”。這樣一來,即便有人因為工廠轉移到東南亞而失業,也不大會認為是印尼或越南的工人搶了自己的飯碗,更不會指望政府替自己出頭。而政府出于維護和周邊國家關系的需要,也更多強調在此形勢下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必要性,這就使得仇外、排拒競爭的言論在中國缺乏擁躉。
中國的全球化是有選擇性的
第三,迄今為止,中國對全球化的擁抱是有選擇性有節制的,主要加入的是經濟和貿易領域的全球化,資本、人員流動、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球化基本談不上,這使得中國可以盡情享受全球化的好處,而避過了相關的風險和陷阱。以人口流動為例:英國脫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盟的開放邊界政策使得移民和難民大量涌入,感覺不堪重負;歐洲近年來頻發恐怖襲擊,原因是過去半個世紀里吸納了太多穆斯林移民又融入失敗;在美國,非法移民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社會議題。而難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在歐美扎下根,是因為這些國家有一系列足以讓難民和移民留下來的政策,比如即便你沒有合法身份也可以就醫上學,費用由政府負擔;久不久會有大赦,非法移民一夜之間就合法了。這些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鼓勵難民和非法移民涌入的作用。
而這些有利條件在中國全都不存在。1982年,中國簽署了《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和《關于難民地位的議定書》,截至2014年8月共接收了約40萬難民,其中包括1970年代末接收的26萬多越南難民和6萬阿富汗難民,1980年代接收的2萬多印度錫克族和斯里蘭卡泰米爾族難民,以及近年來接收的近萬名緬甸果敢難民。這些人在中國基本上是短期停留,多數最終被遣返。而留下來的難民享有哪些權利義務,中國的法律只有一些比較模糊的原則性規定。因此,中國雖然在接收難民,但并沒有建立起長期容留難民的機制,難民沒有在中國工作的權利,難民兒童無法參加高考,這些現實層面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成為主要的難民目的國。
非法移民也同樣如此。在我所生活的廣州,民間傳說有30萬非洲人在此生活工作,官方的數字是6萬,據說其中有些就是簽證過期的非法滯留者。但這些人一來人數較少,無論30萬還是6萬,和廣州近2000萬人口相比根本微不足道,雖然他們中有些人的行為讓本地人看不慣,但畢竟沒有造成大的麻煩,也沒有對本地人的就業生活產生明顯影響,所以大家基本上能相安無事。而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之所以招致激烈反彈,一個重要原因是來的人太多,8000萬人口的德國一年內涌進100多萬難民,對原有的社會秩序和治安沖擊很大。二來中國的政策使得這些非洲人只可能是短期停留,不管在中國待多久,他們基本不可能獲得中國身份,在停留的過程中工作生活子女教育也都會面臨很多障礙,這就大大降低了非法難民長期滯留的可能性。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規定不是中國政府對外國難民和移民的特殊限制,而是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的必然結果,一個湖南人來到廣東打工,其遭遇和這些難民移民也差不多。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全球化的正面態度,是建立在中國的一些特殊國情和策略之上的。但無論如何,在特朗普政府美國利益優先、傾向放棄無利可圖的國際責任的情況下,中國的這一態度,不僅給擔心世界會陷入各國自掃門前雪狀態的企業、個人和國家吃了定心丸,更是中國樹立自由貿易守護者形象、提升軟實力和國際號召力的重大歷史機遇。當然,美國留下的空缺,中國未必就能補上。美國的領導者地位,不僅建立在強大的物質力量之上,也因其為世界貢獻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先進理念、思想、制度、規則,在這些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認為,特朗普的就職意味著“20世紀的舊秩序已經結束,21世紀的秩序以及將來世界會是怎樣還未確定,一切都有可能出現。”在參與塑造新秩序的過程中,中國有選擇的全球化策略必將受到挑戰,而國內改革的推進程度,也將是中國能在新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的決定性因素。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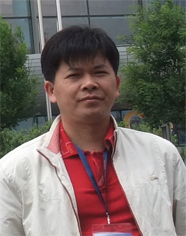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