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是1965年出生的,比我國第一顆人造金剛石的誕生都晚二年。提筆為“中國金剛石五十年紀念文集”寫文章,自己內心的忐忑是真實的,而回首往昔,總想把其時點滴寫出來的沖動也是真切的!一....
我是1965年出生的,比我國第一顆人造金剛石的誕生都晚二年。提筆為“中國金剛石五十年紀念文集”寫文章,自己內心的忐忑是真實的,而回首往昔,總想把其時點滴寫出來的沖動也是真切的!一. 由來
國內的工學博士學位論文通常是“質量與數量并重”,“工藝與理論共存”—無質量無理論似是無水平,無數量無工藝又難以體現工作量;而合成金剛石研究的工藝性是顯然的,且一旦合成不出(不成功)就要冒一個字都寫不出的風險。之所以選擇粉末觸媒合成金剛石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研究方向,既完全是我個人的選擇,也就有它的由來:我本科與碩士研究生都是學材料學的,1989年分配到長沙礦冶研究院材料所工作。當時長沙礦冶研究院材料所是國內金剛石合成用片狀觸媒的主要生產單位,但我卻并沒有從事相關的工作;第一次接觸觸媒材料純屬意外—當時材料所分兩塊:一塊是做材料研究,在科研大樓;一塊是做觸媒生產,在車間。由于當時生產形勢很好,在車間工作的職工待遇很好,夏天有冷飲;而在科研大樓工作的職工似有差距,有時開水都缺;我當時是團總支書記,一時年輕義憤,就帶領在科研大樓工作的20多個人(大都是新近分來的研究生)參加觸媒選片工作。我至今還記得選片的工作場景:兩腳之間放一桶原片,右腳旁放兩個盆,左腳邊放一個盆;一級、二級、三級片就手分出來。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觸媒—實在初級之至。當然,之所以選題金剛石合成主要還是因為自己學過粉末冶金和我也知道世界上第一顆金剛石就是用金屬粉末觸媒合成的。
二. 曲折
1992年,我回到中南大學粉末冶金研究所做博士論文。粉末冶金研究所從來沒有開展過這類研究,也沒有合成設備及相關條件,所以我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找設備。
當時,我們最先找的是長沙233廠(現湖南飛碟超硬材料有限公司),應該是呂海波教授在場,長沙233廠負責同志也很為熱情;而后我再去聯系卻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一是當時大家的生產任務很忙,二是粉末觸媒合成有風險。
于是我們又想到了楊永可廠長。楊廠長原在長沙礦冶研究院工作,后來辭職承包了中南大學機械廠的金剛石車間。略為周折,馬福康院士當時擔任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教育局局長,他也親自出面;楊廠長不僅同意我們用他們的六面頂壓機做合成實驗,而且給我進行了有關金剛石行業知識的“普及”。
原以為只要溫度與壓力條件滿足,從熱力學上講石墨就能轉化成金剛石。第一次合成后,觀察合成塊的顏色都沒變—黑黑的,認為是溫度沒加上去。于是,第二次加了加熱片,第三次也進行了合成塊的改裝。令人心痛的是這頭三次的實驗不僅沒有合成出一顆金剛石,更要命的是每次都裂了頂錘(有時還是一次兩個);實在是無法繼續下去了—因為車間是楊廠長承包的,這里還有他個人的損失。
眾所周知的是六面頂壓機專用性很強,又直接關系各自的經濟效益;而且當時公開的文獻資料幾乎沒有;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小孩是1993年出生的)的統招生(沒工資)。內心的苦悶的確不輕!
馬福康院士是我的論文指導導師之一,他一直關心指導著我的工作。得知我的情況,他直接找到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地勘局湯局長,湯局長安排我到地勘局下屬的北京金地超硬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地公司) 進行實驗,使該研究得以進行,直至完成。
三. 片斷
郊游
金地公司地處北京門頭溝的一個新的工業區,當時入區的企業很少,所以公司孤零零的處于空曠的黃土與茅草中。除了當班與值班的人員,大家下班都是要回城里的;該公司成立不久,也沒有來得及建立相應的文體設施;我真正地又回到了寢室—車間—食堂“三點一線”的大學生活。公司專門給我安排了一臺壓機,可以自由做實驗。開始幾次實驗也沒能合成出金剛石,雖說沒有再裂錘(實在也是不敢了!),但心里的壓力卻是日日沉重!公司總經理邊可正先生是位年過六十的老同志,他原是北京有色地勘局的負責人,有一輛紅色的寶馬車。我每次去時,他都安排人用寶馬車送我去周邊散散心;于是我去了北京的潭柘寺,天津的盤山等地。以當時的情形,我是沒有心情去的(空曠的北國啊,何處才是你動人的風景),而老先生的關愛確永遠都難以忘懷.
險情
一直沒能合成出金剛石,壓力漸大(心中壓力日日沉,何處才是成功門)!有一次,我想是不是因為粉末體的多孔特征,使得合成塊無法密實;于是就把壓合成棒的模具直接放在六面頂壓機中加壓,以求用更大的壓力來獲得更高的合成塊密度。我右手放在控制臺上,眼睛盯著模具—壓到預計的位置就停;不想我手指按的不是“點動”鍵,而是“自動”鍵。等壓到位置,我想停已經來不及了。只聽到一聲悶響,模具炸裂,因為我近視,頭靠得很近。任何一塊裂片都有很大的幾率飛向我的頭,任何一塊飛向我頭的鐵塊都可以要我的命。我揀了其中的一塊,標上日期:1994年8月10日—至今還放在我的書房!先前我做實驗時,車間的工作人員總是要圍著看看“新鮮”,這以后大家就再也不來了。
驚喜
在一次次實驗失敗后,我就粉末的處理,合成塊的組裝與處理以及合成工藝進行了一些改進(現在這些基本是普遍的,而當時是在沒有任何資料下的一個人摸索);從黑黑的(欠溫)與亮亮的(過溫)中看到零星點點的金剛石,到滿斷面的金剛石的光彩,到多晶形多粒級的金剛石,內心的驚喜無以言敘!我是第一時間告訴馬福康老師,馬老師也是放下手中萬忙的工作,第一時間來到車間。我還清楚地記得馬老師俯著身子,眼睛放在顯微鏡的鏡頭上,口里不停在說:健宏,好啊!健宏,好啊!
濺傷
金地公司的設備都是與生產配套的;因此,合成塊的后處理等工作是在中南大學進行的。酸洗提純金剛石工序中有大量含二氧化硫的濃煙排放,在學校實驗室進行很不恰當;我總是在深夜周圍無人時偷偷地進行。記得第一次處理時,因為時間很晚,為了加快速度,我把合成棒敲成粉末后放在一個個燒杯中,燒杯還放在電爐上加熱,算是準備“酸煮”;夏日的長沙十分炎熱,我光著上身,穿條短褲;當把王水倒入燒杯,頓時燒杯中的溶液飛濺起來;不免有些濺到身上,至今我身上還有個小印,也算是紀念了。
繪菜
我在金地公司期間,最喜歡公司食堂的一個叫“繪菜”的菜。一則是因為便宜,大概二角錢一份,只比青菜多五分錢,有時里面還有肉;二則是因為這個菜較咸,內容也很豐富,很合我這個重口味的湖南人;所以,每晚我都要打一份。食堂的“繪菜”常放在最邊上,排隊買的人很少,我就變得顯目起來;時間長了,我總覺得有年輕的師傅們在指點議論。我奇怪就去問,一問才知:所謂“繪菜”就是每天中午沒用完剩下的菜,晚上再混合在一起加加熱的菜。
老師
我指導老師開始是黃培云院士與呂海波教授,馬福康院士是后來加入的。黃培云院士當時年過八十,我只在博士面試時見過;他問了我一個關于濃度與活度的問題。我博士畢業后做了他10 余年的學術秘書,只是這些都是后話了。呂海波教授給過不少的指導—記得當時河北省想引進WINTER 公司的粉末觸媒技術,對方開出數千萬美元的技術轉讓費;因為當時超過一千萬美元的項目是要經國家計委批,于是要組織專家論證;WINTER 公司提供了一個為技術保密而“精心”準備的錄像資料,我看到錄像中從兩面頂壓出來的合成塊斷面上閃閃發光的金剛石倍感振奮。馬福康院士自始至終地關心指導著我的工作:工作開始,他從莫斯科鋼鐵學院請來兩位教授到長沙作人造金剛石學術講座(我也是這時認識姜榮超教授),我所用的粉末觸媒也是他親自聯系俄羅斯圖拉金屬公司提供的;即使是論文撰寫后,他也是逐字逐句進行修改;我記得他在我論文手稿第一頁上寫著一句話:博士論文應該寫出自己一生都可以欣慰的東西!
工人
沒開展這項研究之前,我不僅沒有見過相關的資料與場景,甚至,連一顆金剛石單晶都沒見過,真是一切從頭來!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多人幫助的結果,我無法一一列名致謝。記得在金地公司合成車間主任姓馬,馬主任比我略大些,有很豐富的實踐經驗;他不僅教我很多的壓機操作知識,而且,在我苦悶的時候,我們二個單身漢的交流也給了我很大的安慰。車間有個班長,很年輕,也正在談對象;外貌有些黑瘦,也是外地招工來的;他也常常幫助我做合成實驗。交流中我知道他竟會譜曲,于是,我們還合作了一回:我寫詞,他譜曲。
四. 結果
通過三年多的工作,我實現了用Mn基粉末觸媒在六面頂壓機上合成不同品種(晶形與粒度)與不同轉化率的金剛石。論文寫成后要請專家評審,與大多數同學的論文評審專家由導師擬定不同的是,我的論文評審專家都是我自己擬定的。近20位專家都給于了很高的肯定(大都我至今都沒有見過面)。茍清泉先生不僅給于了評語肯定,還給我寄來了他的相關專著;郝兆印教授不僅給很好的評語,還先后兩次給我來信,既一一指出了我論文中的錯誤與不足,也希望我去吉林大學讀博士后。我的學位論文1996年7月通過了由徐仲愉先生與馬榮駿先生組織的答辯,結果評為優秀。
這里,我簡略的說說論文的主要論文結果:
粉末觸媒的合成:通過溶劑的選擇與處理解決了粉末料的均勻化和氧含量的控制,通過合成塊組裝方式的改進解決了加熱與溫度場的均勻性,通過工藝優化,合成不同品種(晶形與粒度)與不同轉化率的金剛石;并且通過粉末觸媒與片狀觸媒的技術經濟比較,指出了粉末觸媒是合成金剛石的較佳觸媒形態。
內應力機制:高溫高壓下合成腔體內溫度場與壓力場控制的穩定性與精確性是合成金剛石技術的關鍵,而合成腔體內的內應力會直接影響壓力場的分布;片狀觸媒本身因變形而產生的內應力分布不均勻會造成合成金剛石的不均勻。另外,片狀觸媒合成過程中的溫度變化在粉末觸媒合成中可以大大減小。
亞穩態間隙固溶體學說:發現了觸媒成分在金剛石單晶包裹體中的觸媒成份變化的現象與規律,并直接測試了相關數據;在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石墨SP2碳原子向金剛石SP3碳原子轉化過程可以描敘為:石墨SP2以原子團形式熔入觸媒溶劑,形成亞穩態間隙固溶體,并在金剛石熱力學穩定區以金剛石SP3 析出;由此,分析觸媒具有溶碳與成鍵的二種主要作用。
五. 結語
每一項事業的發展都是眾多的人不懈努力的結果。我之所以想把自己的這段經歷寫出來,一是為了記念,黃培云院士2010 年逝世,馬福康院士(我在俄羅斯見證了他獲得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的場景,他也是俄羅斯總統友誼獎的獲得者)2011年逝世,沒有馬先生的幫助指導是不會有我這篇論文的!二是為了學習,研究有不確定性,如何大膽設想,小心求證雖各自不同,然內在的精神是可以借鑒與學習的。
易健宏:1965年生,湖南株洲人;現任中南大學、昆明理工大學二級教授, 昆明理工大學副校長。主要學術兼職有:中國材料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粉末冶金聯合會秘書長,全國材料學科實驗教學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鋼協粉末冶金分會副理事長,中國有色金屬學會粉末冶金及金屬陶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秘書長,中國有色金屬學會材料科學與工程委員會和貴金屬委員會委員,中國機械工程學粉末冶金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鎢業工業協會理事,中國有色加工協會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機協粉末冶金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超硬材料專家委員會委員,湖南省機械工程學會副理事長;《粉末冶金技術》與《粉末冶金工業》雜志副主編,《中國材料進展》、《貴金屬》與《中國鎢業》雜志編委。


 手機資訊
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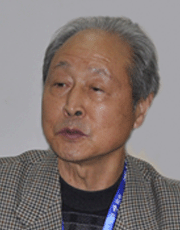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46號